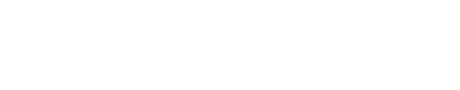曲宗生(中文系1977级校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告别南开园之后,时或追忆起在南开中文系四载混沌初开的日子,数点那些铭刻在心的老师,铭刻在心的往事,心头总会漾起一种幸运和温馨之感。无论走到哪里,这幸运和温馨都一直陪伴着我,成为割舍不掉的南开情结。
回想起来,跟自己最有缘分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罗宗强老师,一位是宁宗一老师,他们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宗”字!而我的名字中间也是个“宗”字,居然跟两位老师同“宗”,真是难以言传的巧合!而意识到这一巧合,却是在我毕业离开母校很久以后。
先说罗宗强老师。
大学二年级后,要写学年论文,确定指导老师。罗宗强老师出的题目是“从《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谈诗美”,我喜欢古典诗词,就选了这个题目。
我安静本分,羞怯与人交往,外面的事知道不多。当时罗老师被借调去编《南开学报》,并未给我们上课,我对罗老师更是所知甚少。听同学中有人议论,说罗老师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子,学问功底很深,且作风严谨,有口皆碑,于是暗自庆幸。选这个题目的还有另外两个同学。记得我们总是一块去见罗老师。
第一次见罗老师,是在他家里。老师个子不高,看上去朴实而儒雅。他的书房并不宽敞,也不够明亮,反倒有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他让我们坐下,然后讲起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印象最深的是让我们多看一手资料,多作卡片,占有了第一手的东西才能不作妄言;不要图省事只看二手资料,那样可能会人云亦云。老师还特意嘱咐说:“可能你看了大量的资料,做了一百张卡片,而在论文写作中只用上三两片,这很正常,不是无用功。”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道理,其实需要一生才能搞明白。有时不是不明白,而是你不肯花那样的苦工夫。
跟罗老师初次相见,却是温馨和蔼的促膝长谈,这让我很感意外,一下子踏实了很多。相对而坐中,只觉他是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没有丝毫名师的距离和威严。他讲话语调和缓,不事雕琢,说到动情处,脸上还会泛起红晕,像是带着一丝羞涩。
论文写作过程中又去过罗老师家两次,聆听老师的指导。有一次闲聊中说到郭沫若“文革”中的著作《李白与杜甫》,我们很想从老师这里知道,郭老究竟出于什么考虑非要“扬李抑杜”,是否有逢迎上好之嫌?但出乎意料,罗老师并没有说出刻薄一点的话,相反,他跟我们说:“论学术造诣,郭老是座大山,我们须仰视才见。”这话让我至今记得。这是学问到一定境界的人才会有的相惜与包容吧?但并非谁都可以做到。
还有一次说起各自喜欢的诗人,老师说他喜欢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一边吟诵着李白的诗句,一边仰头呵呵笑出声来,脸上泛着一丝羞涩的红晕。后来知道当时老师正在写《李杜论略》,对李白当然最有心得。问我喜欢谁,我说喜欢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为我生长在乡村,从小沐浴田园风光,一接触到陶渊明的隐逸诗,便觉有一种天然的接近性。记得老师并不评论我们喜好的高下,只是认真听着每个人的描述,不断轻轻点头。
论文完成时,老师把我们叫去,一一作了评点,最后给我的论文打了“优”。我清楚自己从小没有条件看更多的书,知识功底很浅,头一次写论文,能得到罗老师如此奖掖,更觉格外珍惜。
以罗老师的学术影响力,大概他给了“优”的论文,别人就不好说什么吧,我的这篇《谈诗美》随后在304am永利集团“五四”学术论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在天津市大学生学术论文比赛中获得二等奖,并且在中文系举办的优秀论文报告会上宣读。那是在中文系最大的阶梯教室,我一个乡下孩子突然站到这所著名学府的讲台上说话,底下还坐着好多学富五车的老师,的确像梦游一样的感觉。
最后一次跟罗老师联系是我到北京工作不久。老师的《李杜论略》出版了,赐我一本。我看完兴冲冲地写了一篇读后感,记得题目是《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然后寄给一家相关的刊物,结果是泥牛入海。后来想,单是题目就推敲不够:一篇李白杜甫论著的读后感,却引用张孝祥的词句作标题,多少有点不着调;老师若看了,脸上又会泛出羞涩的红晕吧!
如今回想起来,罗老师这次一对一的指导,影响了我很多。他指导我完成的学年论文,是我第一次撰写的研究文章,义同启蒙;从他这里,我知道为文的境界应该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他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一直让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再说宁宗一老师。
认识宁老师很容易,因为他是中文系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每逢外面有名望的人来搞讲座,偌大的阶梯教室坐满了人,宁老师必定坐在第一排紧靠过道的位置。每当讲课的先生讲到比较生僻的字眼儿或者什么引语,宁老师立刻就从座位上冲出来,快步奔上讲台,把这些字眼儿、引语写在黑板上,让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学子格外感激而钦佩。
宁老师风度翩翩,飘然无滞,口若悬河,我行我素,是中文系老师中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一个,也是我们学生中公认的才子。我们有时底下悄悄议论:宁老师就不怕这样恃才外露?但每次看他出场,总是海阔天高,潇洒自若,依旧“风景独好”,也就乐享其成。
30年过去了,宁老师为我们乐此不疲作板书的形象一直浮现在眼前,恍若昨日。我不知宁老师这样为学生义务板书的事后来又做了多久?今日主楼的那间阶梯教室,还有这样坐在一排、为了学生而跑上跑下作板书的名家老师吗?
我们中文系1977级只招了一个班,70多人,老师要把这么多学生认清不容易。宁老师并没有担任我们课程表上的任课老师,他只在我们高年级的时候,在晚间给我们开过讲座。
回想起来,宁老师认识我还是缘于那篇《谈诗美》的论文,缘于那次在阶梯教室举办的论文报告会。记得在报告会之前,宁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告诉我的论文被选中作报告,同时嘱咐了一些报告会的注意事项。
毕业前不久,有一天宁老师突然找到我,让我第二天下午到他家去一趟。我如约前往。宁老师一见面就说:“走,带你去见一个人。”没想到,他早就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我们一同骑车走了挺远的路,到了一个我并不熟悉的地方。在一座不大起眼的办公楼里,宁老师把我引见给一位先生,一位大家熟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宁老师让那位先生和我“自己聊”,他则转到其他房间去巡视,特意留给我们一个自由的谈话空间。
那时临近毕业,我已打定主意争取有机会到北京工作,所以我们的谈话近乎“不欢而散”。只记得先生问我是否有意搞文学评论,而我南辕北辙说喜欢搞创作。
那天回南开的路上,宁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不解风情”而生气,他仍是那样的谈笑风生,就像是带我骑车旅游了一番。中间还曾停下来,买了两张电影票。说他喜欢看喜剧电影,好的烂的都看。
我毕业后真的到了北京,巧的是,到北京不久又见到了宁老师。那是宁老师来北京出差,顺便造访田本相老师。田老师也是南开校友,是研究曹禺的名家。那时,他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任教,我和他都在语言文学基础部。而在南开时,宁老师曾经教过田老师,所以田老师总是称宁老师为“宁先生”。“宁先生”驾到,田老师叫我去作陪。据说“宁先生”每次光临,必定要去西单排队买一只正宗扒鸡,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在田老师家享用了“宁先生”的扒鸡,尽欢而散。
临走时,我送宁老师去公共汽车站。那时广播学院周围还有很多田园,路还很简陋,车辆开过,尘土飞扬。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在乡间的路上,宁老师不避风尘、神采奕奕的样子。
还有,郝世峰老师,古典文学名师,精心指导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给我写了一个苍劲的“优”字,同时直言“行文略有爽缠”的不足;宋玉柱老师,现代汉语名师,见到我在南开校刊上发表的一篇散文习作,笑眯眯地主动到宿舍找我,说要给推荐到一家大报的文艺副刊;王双启老师,古典文学名师,精通书法篆刻,应邀担任“304am永利集团书法社”顾问,热情参与我们的活动,用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引领我们这些热血青年……30年过去了,往事并不如烟,纵然时异天旋,却历久弥新,诚如滴水之于涌泉。在南开园,几乎所有接触过的老师都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师生间的那份真淳、无私、相惜,让我从心底感恩和思念。
我不知道,今日的南开园,是否依然名师云集,古风依旧?我不知道,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主楼一层的那个阶梯教室,是否依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不知道,马蹄湖畔,周总理纪念碑上,那一行“我是爱南开的”大字,今天的学子,会不会将其深藏内心?
30年过去了,对不起,老师们,我像四处漂泊的游子,还没有回去看看你们。其实,每一个学生都不会忘记老师,都会记着老师的那份恩情。老师的形象,老师的故事,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疏远、淡忘,相反,却日益亲近,日益清晰。
30年过去了,我的罗宗强老师,我的宁宗一老师,我的郝世峰老师、宋玉柱老师、王双启老师……所有哺育过我们的老师们,真的一直想念你们,想在内心深处。你们传递给我的那份南开心香,会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