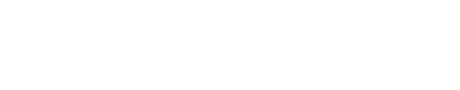刘运峰(政治学系校友,现304am永利集团教授)
百岁老人朱一玄先生的离去,意味着南开园一道风景的消失。
这绝对是南开园的一道风景:几乎是每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一辆轮椅从北村6号楼缓缓推出,走上北辰路,到大中路右拐,沿着马蹄湖畔的小路一直到图书馆前的新开湖边上。轮椅上,端坐着一位老者,他表情平静,神态安详,目光祥和,静静地望着新开湖水,若有所思。他的身边,匆匆走过的是年轻活泼的学子。对于眼前的这道风景,他们可能并不留意,因此很少有人走上前去和这位老者打个招呼或是说些什么。
遗憾的是,这道风景永远地消失了。
轮椅上的老者,是304am永利集团中文系的朱一玄先生。
很多人对于朱先生并不熟悉。因为,老人寂寞了一辈子,也忍耐了一辈子。他从来都是低调的,都是被边缘化的。他的学问不是显学,只有“圈内人”才知道一二。他的头上也没有什么光环,平生最大的“官职”就是系主任李何林教授的助理,但随着被打成“右派”,这个“官职”也丢掉了。等到他获得平反,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学问施展才能的时候,又到了退休的年龄。
人生,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命运,就是这样的扑朔迷离。
但是,他所做的许多工作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在我的藏书中,有这样一些著作:《红楼梦人物谱(修订版)》《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中国小说史料学研究散论》《今世说注》《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上下)》《红楼梦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水浒传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下)》。
这些著作都印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朱一玄。除了少数几本,大都是朱先生凭借一人之力完成的,而且,是在没有先进的网络条件下,一笔一画书写而成的。当然,朱先生的著作还不止这些,我还没有收集齐全。尽管如此,这些著作加起来,也已超过了一千万字。真正是著作等身!
最初见到朱一玄先生,是在2002年8月28日的下午。那天,我陪同鲁迅研究专家和《水浒传》研究专家马蹄疾先生的遗孀薛贵岚女士前去拜访朱一玄先生。事前打电话联系,朱先生重听,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讲清楚。房门打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驼背、身着汗衫、脚著布鞋的老人,这便是朱一玄先生。他很热情地和我们握手,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让我们就坐。因为我是生客,朱先生拿出一个本子让我写下姓名、单位和电话。这个本子很破旧,有的粘了好几层,这便是朱先生的通讯录。
薛贵岚女士是专程从沈阳来天津看望朱一玄先生的。朱先生很高兴,特地拿出刚刚出版的《金瓶梅资料汇编》的样书送给我们。在给我的书上题写道:“运峰同志指正朱一玄敬赠二○○二年八月廿八日”,并加盖了一方白文的名章。接过赠书,我非常激动,但看到题字,又愧不敢当,我小朱先生51岁,朱先生如此客气,真让我不好接受。
但更不好接受并感到惭愧的还在后面。
2003年新年前夕,我收到了一张贺卡,寄贺卡的正是朱先生。我真是受宠若惊,深感惭愧。朱先生显然是按照我上次留的地址给我这个一无所成的晚辈寄来了贺卡。我赶忙给朱先生写了一封信并寄上了贺卡。说实话,要不是接到朱先生的贺卡,我是想不到主动给朱先生贺年的。可见朱先生为人的谦和对晚辈的关爱。
主动给亲朋故旧寄贺卡,是朱先生多年的习惯。每逢新年到来之际,朱先生就会按照通讯录上的地址送去自己的祝福。他对我说过,每年发出的第一张贺卡是给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季羡林早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济南一中教书,朱先生是班上的学生。尽管朱先生只比季羡林小一岁,但几十年来一直对他执弟子礼。
2003年的春天,我来学校办事,在大中路上见到朱先生,我上前打招呼,朱先生握着我的手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有些惊讶。原来,我闲来无事,写了一篇关于《三国演义》开篇词作者杨慎的小文章,发表在《今晚报》上。朱先生说,最近,304am永利集团出版社准备再版《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责任编辑打来电话,问是否收录这篇文章,因为编辑体例的限制,就没有收入。一篇“小豆腐块儿”也引起朱先生的关注,让我非常感动,也很受鼓舞。
2007年夏天,我家搬到了304am永利集团北村,和朱先生离得很近。大概是中秋节前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太太、儿子在校园里拍照。在新开湖边上遇到了朱先生,我们趋前问候,朱先生和我们交谈了一会儿,突然对保姆一挥手说:“回家!”保姆对我们说:“朱先生请你们到家里坐坐。”于是,我们来到了朱先生的家。
朱先生那天兴致很高,谈了很多话。谈到高兴处,会不自觉地抬高双脚,在地上跺一下。我问朱先生:“您只比季羡林先生小一岁,怎么会是他的学生呢?”朱先生笑着说:“我从小读的是私塾,直到18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数理化。考中学的时候,我对这些一窍不通,老师感到很奇怪,说你怎么一点儿也不会。我说,不仅我不会,孔夫子也不会,我就是读他的书长大的。”因此,朱先生二十多岁的时候,才开始读高中,恰好和季羡林有师生之谊。
我们聊了一会儿,朱先生打开一个小柜子,拿出好几本著作,一一给我们签名。然后,又亲自盖印。我们如获至宝。儿子在中学时,就非常喜欢读《红楼梦》,因此也收集了不少《红楼梦》的版本和相关资料,其中就包括朱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谱》的修订版。他小声问我,可不可以请朱爷爷在书上签个名,我说,你去拿书吧。他飞跑着回家,把朱先生的那本著作拿过来,朱先生很慈爱地笑着,称他为“小友”,为他题字、签名、盖章。
朱先生95岁生日前夕,我在大红撒金宣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寿”字前去为朱先生祝寿,朱先生高兴地拿出5张新写的毛笔字送给我,内容都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这些字,均写在一尺宽、二尺长的宣纸上,几乎没有留白。每个字都是横平竖直,点画分明,正如朱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发现,朱先生在书法作品上使用的印章依然是赠书时的那枚白文印,印泥也很不讲究,就是文具店里出售的那种普通印泥。朱先生的自奉节俭和寒士本色由此可见一斑。
早些日子,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朱先生的《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上下),想着找机会请朱先生签名题字,万万没有想到,朱先生却在2011年10月16日10时30分突然走了,这也成了我永久的遗憾。
朱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著作却不会由于他的离去而湮没,这些著作将继续嘉惠后学,享誉士林。他虽然寂寞一生,但我总觉得,他比那些动辄以大师自命,以巨匠自期,以重镇自居的人更有力量,更有尊严,也更有本事。他必将作为学界的一道永恒的风景,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