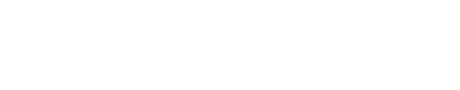周 荐(中文系1977级校友,澳门理工大学教授)
今天——11月5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了,可连日来似乎总是寝食难安,今日尤甚,总感觉有点儿什么事情要发生,可又不知会发生什么。下午鬼使神差的打开早已不用的那个亿邮信箱,大师姐刘道英教授的一封中午紧急发来的邮件一下子攫住了我的眼睛:师弟,咱们的宋老师已于11月1日去世,而且已经火化了,我也是今天上午才得到的消息……惊愕的同时,泪水夺眶而出,眼前的一切顿然模糊起来,只剩下几个碎片在眼前晃动。
宋玉柱师留给我脑海里的第一个片段是34年前,我们中文系七七级本科同学走进南开第一个学期所上的“现代汉语”课。我们进入大学,不再像此前一样有所谓“上管改”的任务,而完全是拜师、求学、搞研究,老师们似乎也一下子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找到了感觉,希望倾其所有将自己的学问教授给学生。当然,老师们对学生的要求,也就比之前严厉得多了。邢公畹先生、张清常先生、朱维之先生、王达津先生等名教授纷纷走上讲台给我们这些本科生授课,老师们不苟言笑的严谨治学的风格在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玉柱师的严厉却更为著名,乃至于34年后的现在还常被同学们忆起。记得有一次,玉柱师已开始讲课,一位同学姗姗迟到而径直走进教室,这让玉柱师颇为不快;紧跟着玉柱师提问,一位同学回答不上来,于是乎玉柱师勃然大怒,厉声呵斥。其实当年的宋老师,不过45岁,比今天的我还年轻整10岁。玉柱师的雷霆震怒,令全班同学十分惊悚,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他的感情是敬畏多于亲切。那个学期结束,我赴南方省亲,在火车上恰巧与玉柱师“遭遇”。老师当时就站在我面前,望着我,仿佛期待我张口喊他一声,而我嗫嚅了半天却终究未能张开口叫他一声“老师”,脸胀得通红。玉柱师见此未置一词,返身走开了。
然而我这样的大不敬,似乎并未导致玉柱师对我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毕业分配时,系里要留文学专业、语言学专业各一名助教。文学助教毫无疑义的选定了李瑞山同学,语言学这个助教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玉柱师看好一位张姓女同学,这位女生毕业前已有不错的论文发表;而当时的我对语言学几乎可以说是懵懂无知,也似无多大兴趣,对研究作家浩然倒是兴致蛮高(一点题外话:今年10月6日在学校举行的七七级七八级毕业30年大返校活动中,张学正老师见到我仍对我当初未再继续我的浩然研究“耿耿于怀”),我后来的研究生导师刘叔新师说他“发现”了我,坚持认为我有词汇学的天分,力劝我把兴趣转移到词汇学上来,并力主留我做助教。玉柱师也就并未再为那位女生多说什么,很爽快的便同意我留在教研室工作。说心里话,很长一段时间,我极担心在宋老师身边学习、工作自己会有麻烦,但是后来的一切却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第一次上讲台前的试讲,教研室的老师们都出席了,玉柱师、陈坚师尤其热情地给我指出问题所在;我第一本书出版时玉柱师似乎比我还高兴,告诉我他第一本书出版时,心情仿佛是自己的孩子出生;我曾几次有机会与玉柱师一起到蓟县、北戴河等处参加命题工作,玉柱师都非常慈祥地嘱咐我做这做那;甚至玉柱师回昌黎老家探亲时还不忘带来自家梨树上结的硕大的梨子给我品尝。更让我永生难忘的,是1990年高级职称评聘前夕,玉柱师突然打电话给我,略带责备的口吻问我:你为何还不将你的论著材料报上来?我说自己不够格。玉柱师斩钉截铁道:我看完全够!他还叮嘱我把自己的材料复印了给包括他在内的中文系各评委送去。我又胆怯了,说:我从未到各位老师家去过,如今为了评职称去人家,怎么好意思?玉柱师立刻说:怕什么?你不敢,就把材料统统交给我,我替你散发给各位!就这样,那一年我破格晋升了副教授。1996年,又是玉柱师鼓励我申报破格教授的职位,并获得了成功。直到那一年,我才找了个恰当的时机,对先生就1978年暑假火车上的失礼表示歉意,但玉柱师只大度地一笑,什么话也没说。玉柱师不是我研究生的导师,然而他所给予我的恩遇却远不止此。有一次,我的导师可能是因为误听了一些传言而对我产生了一点点误解,玉柱师竟不顾惜他们老同学的颜面,为我投书报章仗义执言。彼时我正在国外工作,几个月后回国听说此事,久久不能言语。我知道两位老师都是因为关爱我才打起那场笔墨官司,至今深感对不住两位恩师。
玉柱师因为妻女是农村户口,又无工作,只靠他一人的微薄薪水养家,曾十分清贫,无奈之下,于90年代初调离中文系到了薪酬略高的汉语言文化学院去工作。记得先生调离前,我作为教研室的秘书专门组织老师们开了个话别会,系主任罗宗强先生也赶来参加。大家都为玉柱师离开工作了35年的中文系而惋叹,同时也祈盼先生的生活条件能因此而得到一些改善。很快的,日本北九州大学邀请先生讲学五年,先生的境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玉柱师再也不需要为了几元钱的稿费而赶写那些小稿子,似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了,然而病魔不断袭来,令先生的身体明显的一年不如一年了。尤其是师母病故后,玉柱师瞬间变了个人似的。还记得,送师母走的那天大雪纷飞,总医院的殓房外,非亲属的我也踏雪前来送老人最后一程。回到南开,去见老师,老师只默默的与我对坐,一声叹息之后,接着眼圈就红了,始终未出一言。握着老师颤抖的双手,望着他的皤然白发,我蓦然感到,我的玉柱师,仿佛一下子衰老了10岁!2008年我的工作重心南移后,几乎每年回校都必定去看望恩师,向他汇报工作生活情况,每次他都慈祥地望着我,听我讲说外边的情况,不时的勉励几句。本来今年10月初大初返校时我是要去看望老师的,但由于时间实在太紧,担心看望了这位老师没有看望那位老师多有不妥,也由于不久前刚与玉柱师通过电话,料他身体并无大碍,便与妻约定今年12月圣诞假回津时一同前去看望包括玉柱师在内的几位师长。孰料造化弄人,一念之差,竟与恩师天人永隔,怎不令人扼腕太息!
玉柱师可谓一介布衣,一生中连个小组长的职务都未担任过;由于调入汉院这个教学单位,退休又早,也未能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但他从容淡定,从未以此为意——他从不以得到什么飞来之福而喜,也从不以未得到什么本该得到的东西而悲,该做什么照做什么,终于以自己的斐然的学术成就而在汉语语法学史上拥有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地位,在一代又一代学生心中树立起了一座堪称师范的丰碑。
整整一个下午,整整一个晚上,我眼前晃动的都是玉柱师的形象——34年前他在黑板上奋笔疾书的形象,在讲台前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的形象,沉吟时字斟句酌的严谨形象,问题终获解决时挥动手臂的潇洒形象……玉柱师其他年龄段的片段也偶或出现在我眼前,但他45岁时的英姿却在我心中定格,永难在我脑海中磨灭。玉柱师去了,他不是以79岁的高龄蹒跚老去,而仿佛是以45岁的英年驾鹤西游。他还会回来的,来给我上课,依然是那般沉稳淡定;他即使不再归来,终有一天我会去看他,继续听玉柱师讲课,他依旧会是那般严谨睿智。我的玉柱师永远是那么年轻,洒脱,因为他留给我的那个片段是45岁,比我今天的年龄还年轻10岁,比我去看他时可能还要年轻更多。有一首歌唱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玉柱师也是这样,他不死,不老,永远与我同在,永远那么年轻!
2012年11月5日夜至6日凌晨四时濠江灯下